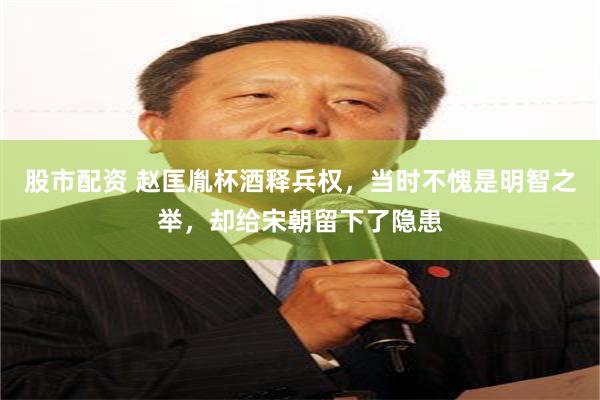
赵匡胤夺取政权后,为防止重蹈五代旧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亲兵禁卫领导体制进行调整。
宿卫亲兵将领的除授呈现出以功臣代宿将、以亲信代功臣、以亲兵代亲信的过程,达到了军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的目的。
而我们熟知的“杯酒释兵权”也是赵匡胤的手笔,那么,看似简单的酒宴背后到底隐藏的是什么呢?
以功臣代宿将
建隆元年(960年)正月十一日,加封拥戴有功将领,开始着手调整亲兵禁卫领导体制:论翊戴功,以周义成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为归德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武信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殿前都虞候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虎捷右厢都虞候张光翰为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龙捷右厢都指挥使赵彦徽为武信军节度使。
正月十九日,又“加(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昭化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二品,(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这次调整,需要注意的是赵匡胤为更好地控制殿前军与侍卫亲军,将二者实际最高指挥官进行对调。
石守信作为宋太祖亲信,由殿前都指挥使调任侍卫亲军司副都指挥使,实质上成为了侍卫亲军的最高统兵官,也就替赵匡胤看住了侍卫亲军。
由于在陈桥兵变中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被杀,侍卫亲军中实力最强、地位最高的就成了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赵匡胤将其调往殿前军出任副都点检,名义上是加官进爵,实则是削弱了其在禁军中的影响力。
须知此时的殿前军都指挥使是在陈桥兵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王审琦,同时也是赵匡胤“义社十兄弟”的核心成员,殿前都虞候更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高怀德实际上不能对殿前军进行有效指挥。
留任的侍卫亲军司高级将领张令铎是军中出了名的老好人,在侍卫亲军司中又处于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对新生的宋政权构不成威胁。
二司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韩令坤则领兵在外,实际上不能指挥本司事务,军权还是落在了兵变功臣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手中。
通过这次晋升,赵匡胤初步掌握了亲兵禁卫。
在平定李筠叛乱后,宋太祖解除侍卫亲军司马、步军都指挥使张光翰、赵彦徽的军职,代之以原殿前司部下韩重赟、罗彦瓌,进一步控制了侍卫亲军司。
到建隆二年(962年)闰三月,在平定李重进叛乱后,又解除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二人的禁军军职,外放为节度使。殿前都点检一职遂“不复除授”,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由副都指挥使石守信升任。由此,宋太祖基本上实现了兵变功臣对后周留任大将的替换。
以亲信代功臣
但以兵变功臣掌握兵权仍不能确保赵氏江山千秋万代,五代以来的禁军颠覆仍令赵匡胤心有余悸,在枢密副使赵普的反复劝谏下,赵匡胤决定继续替换亲兵禁卫的指挥体系。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赵匡胤召集石守信、王审琦等“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的兵变功臣宴饮。宴会中也直白地表述了对五代以来禁军将领犯上作乱的担心。
第二天,禁军诸将“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与结婚姻。
”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皆外放为节度使,虽然石守信仍兼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但也是“其实兵权不在也”。高怀德去职后,殿前军副都点检一职“自是亦不复除授”。
兵变功臣先后被外放并解除禁军军职,后周以来和赵匡胤“昔常比肩,义同骨肉”的禁军中高级宿将被一扫而空,禁卫亲军中再无可匹敌赵匡胤资历者,赵匡胤也由此也进一步凝聚了在禁军中的威望。同时,禁卫亲军中的高级职衔也不再除授,使禁卫亲军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并且“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使之再次沦为皇权的附庸,避免了亲兵禁卫将领的失控。
“杯酒释兵权”后,亲兵禁卫再无宿将统领。
随后,赵匡胤欲以当时名动天下的名将,同时也是赵氏姻亲的符彦卿典领禁军,却被赵普极力阻止。
须知宋太祖赵匡胤是乾纲独断、“亲总庶务”的开国之君,赵普虽为其所倚重的亲信谋主,但国家的大政决策还是掌握在宋太祖一人的手中,赵普也只能在赵匡胤的意图之内发挥个人作用,这是一个绝不可逾越的分寸。
两司管军将领的人事安排是赵匡胤代周建宋后防止重蹈五代禁军作乱旧辙,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赵普的劝谏必须也要符合宋太祖赵匡胤以功臣代宿将,以部下代功臣,再以亲兵代部下的总体思路和既定方针。
在赵匡胤偏离这一方针,欲以姻亲统军后,赵普自然可以极力劝谏,并隐晦地指出任用符彦卿这种“名位已盛”的将领管军可能对赵宋政权带来的威胁,促使赵匡胤收回成命,仅赐“袭衣、玉带”。对两司管军的除授回到了“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的故辙上。
以亲兵代亲信
赵匡胤通过金银、田宅、官爵、婚姻等方式,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一步一步地赎买了后周时期留任的禁军宿将以及与自己“昔常比肩,义同骨肉”的功臣将领的禁军兵权,代之以原殿前军嫡系部下,弥补了自身“姓字且不闻于人间”的不足,加强了对亲兵禁卫的控制。
同时撤销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副使,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四个禁军高级职衔,从政治上降低了禁军将领的地位,防止其日后失控。
在平定李筠叛乱时,面对李筠这种可以“比肩”的宿将,赵光胤近乎以哀求的语气劝说,“我未为天子时,任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少让之邪?”至于高怀德、张令铎这种典军宿将更是“慰抚赐赉甚厚,或与之结婚”主动结为姻亲,极力拉拢。而随着“比肩”将领的陆续外放,以及“易制者”的陆续升任,赵匡胤对亲兵禁卫的掌控力不断加强,对待禁军中高级将领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乾德元年,赵匡胤听信史珪、石汉卿的诬陷,认为时任殿前都虞候的张琼豢养私兵,即令二人拷问,“(赵匡胤)令击之,汉卿即奋铁挝击其首,气垂绝,乃曳出,遂下御史府按鞫。”几乎当场将其打死。到乾德四年,又有人谮称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同样引起了赵匡胤的极度不满,“欲诛之”。幸亏赵普“开陈愈切”地及时劝谏:“亲兵,陛下必不自将,须择人付之。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复为陛下将亲兵者。”虽然赵匡胤采纳了他的劝谏,没有将其处死,但将其解除禁军兵权,领其出镇地方。
但也造成禁军诸将“人人惧罪”,都虞候杨信更是于同年突然染上怪病,丧失了语言能力,入朝上奏,军中传令全凭一名家奴传达。杨信虽然残疾,但太祖仍照旧令其典军,直到死前一天又离奇痊愈,不得不令人生疑这些深刻反映了此时禁军政治地位的下降。
此后,殿前都指挥使一职更是空悬六年,殿前司高级军官只余都虞候一人。
侍卫司将领,主要以赵匡胤原殿前司亲信部下群体为主,直到宋太祖去世,侍卫亲军管军将领大致仍属于这个群体。开宝六年(973年),太祖朝最后一任侍卫亲军管军,即由原殿前军铁骑军都虞候党进出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原殿前军左射指挥使李汉琼任侍卫马军都虞候;原殿前军内殿直都虞候李进卿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原殿前军控鹤副指挥使刘遇任侍卫步军都虞候。
相对于侍卫亲军,殿前军更多地承担护卫宫禁保护皇帝的职责,管军人选直接关系皇帝安危和王朝兴废,赵匡胤更多地选用原殿前军的亲兵卫士群体来充任管军。
一方面,这些亲兵卫士往往是赵匡胤的“腹心”,对赵匡胤本人很忠诚。“汝曹皆我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另一方面,他们本身资历浅薄,至“陈桥兵变”时,多数人仍为普通军兵,仅少数人出任下级军官,“人望”不足,他们能够出任殿前军管军完全是出于和赵匡胤的特殊关系,仰仗着赵匡胤的宠信,不敢丝毫忤逆,更不可能反抗。
该行维持对中国中免的“买入”评级,但将目标价从102.4港元下调至65.5港元。
建隆二年(961年),赵光义改任开封府尹后,殿前都虞候一职便由“世为牙中军”且“隶太祖帐下”的张琼接任。乾德元年张琼被赵匡胤当殿杖杀后都虞候一职由原“麾下为裨校”的杨义充任,开宝六年再升任殿前都指挥使。
除了殿前指挥使杨义之外,还有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控鹤左厢都指挥使崔翰,殿前指挥使、都虞候米信、石汉卿等赵匡胤原亲兵卫士执掌殿前军。
他们依仗与宋太祖的特殊关系,在殿前军中肆无忌惮,张琼“自作威富,禁旅畏惧”,石汉卿“恃恩横恣,中外无敢言者”。这种情况下,殿前司虽然保留了李重勋这样“与太祖同事周祖,谨厚无矫饰,太祖甚重之,故擢委兵柄,始终无易”的宿将,但在以赵匡胤原亲兵卫士掌控的殿前司中,难以有所作为,只能表现得“谨厚”,成为妆点政权安抚人心的吉祥物了。
自乾德三年(965年)始,赵匡胤“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取藩镇精锐以补禁卫,驻防地方的责任逐步转移到禁军身上,二司特别是侍卫亲军司的镇戍职能逐渐超过了宿卫职能,开启了亲兵宿卫国防军化的进程。殿前司禁军除驻防地方外,还有班直以护卫宫禁,“其尤亲近扈从者,号‘班直’”。
至此,通过“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人事变动,在重视和优容前朝宿将,抚慰元老勋旧,给予良好的经济待遇并与之通婚结成政治联盟的基础上较为和平的解除了他们的禁军军权。
禁军两司管军完全由赵匡胤原殿前军低级部下改任,基本杜绝了五代以来禁军变乱的隐患。
同时一方面裁撤禁军高级军职,降低了两司管军的政治地位,使之无力挑战枢密院的领导。另一方面许多管军高位长期空缺,防止出现典军宿将,另以毫无“人望”的近幸将领出任管军,便于皇帝居中操纵,从而将全部禁军的全部兵权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同时,从“卫士”或“随龙人”中拔擢殿前司管军,以强化皇帝自身的安全;从“部下”中选拔侍卫亲军管军股市配资,以强化对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形成了“拔擢亲卫”与“受任浅资”的用将原则,“从而形成了宋代很有特色的,以‘潜邸’之攀附旧人甚至奴仆来统领三衙禁军的传统”。这种做法一直为后世君王所沿用,成为“祖宗之法”。
亲军禁军赵匡胤侍卫亲兵发布于:天津市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网上配资开户网_股票网上配资_网上炒股门户网站观点